
紀錄片女導演米歇爾·波爾特拍攝的《在欲望之所寫作:瑪格麗特·杜拉斯訪談錄》由法國國家視聽研究院出品,曾在法國電視一臺(TFI)播出。諾夫勒堡的房子(上圖)、花園、森林、大海……杜拉斯待過的這些地方如何變成“故事的承載者”,如何建構起某種地理詩學?這個訪談為杜拉斯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的珍貴資料。本文選自根據采訪記錄整理而成的同名圖書(黃葒譯,南京大學出版社即將出版),由出版方授權刊發(fā)。
——編 者
瑪格麗特·杜拉斯:聊諾夫勒堡的這棟房子、聊花園,我可以聊上幾個小時。我知道一切,知道以前的門在哪里,一切,池塘邊的圍墻,所有花草,所有花草在哪里,甚至那些野草我都知道它們在哪里,一切。
米歇爾·波爾特:瑪格麗特·杜拉斯,您寫過:“我拍電影是為了打發(fā)時間。如果我內心強大到可以什么事都不做,我會什么事都不做。正是因為我沒有強大到讓自己無所事事,我才去拍電影。沒有任何其他理由。關于我所做的事,這是我能說的最實實在在的話了。”
杜拉斯:的確。
波爾特:您是不是也會用同樣的方式說:正是因為我沒有強大到讓自己無所事事,我才寫書?
杜拉斯:當我寫書的時候,我不會有這種想法,不會。通常都是我停止寫書的時候,我才會有這種想法。我想說的是,當我停止每天寫作時,我才去拍電影。只有當我停止寫作,我才停止,是的,我才停止某種……呃……說到底,發(fā)生在我身上最重要的事情,也就是寫作。但我最初寫作的理由,我已經不知道是什么了。或許和下面的理由一樣。讓我驚訝的,是并非所有人都寫作。我對那些不寫作的人暗自欽佩,當然,對那些不拍電影的人也一樣。
 瑪格麗特·杜拉斯在諾夫勒堡的房子里
瑪格麗特·杜拉斯在諾夫勒堡的房子里
波爾特:您的很多電影都發(fā)生在一棟和外界隔絕的房子里面。
杜拉斯:在這里,是的,在這棟房子里。每次我在這里,每次我都有拍攝的欲望。會有一些地方給你想拍電影的欲望。我從來沒想到一個地方會有這種強大的力量。我書中所有女人都住在這棟房子里,所有。只有女人才會在一個地方住下來,而男人不會。這棟房子就曾住過勞兒·瓦·施泰因、安娜-瑪麗·斯特雷特、伊莎貝爾·格朗熱,同樣也有各種各樣的女人;有時候,當我走進這棟房子,我感覺……有很多女人都在這里,就是這樣。我也曾住在這里,完完全全。我想這是世界上我住得最多的地方。當我說到其他女人,我想這些女人身上也有我的影子;仿佛她們和我是彼此相通的。她們在屋子里待的時間,就是話語到來前的時間,男人到來前的時間。男人,如果他無法給事物命名,他就會感到苦惱,感到不幸,感到無所適從。男人不說話難受,而女人不會。我在這里見到的所有女人一開始都沉默不語;之后,我不知道她們會怎樣,但開始她們都一言不發(fā),久久沉默。她們仿佛嵌在房間里,融入到墻壁、房間的所有物品里。當我在這個房間里,我有一種感覺,不要改變房間固有的秩序,仿佛房間自身,或者說住所并沒有覺察到我在那里,一個女人在那里:她在那里已經有她的位置。或許我談論的是這些地方的靜默。
在中世紀,男人們要么去為領主打仗,要么參加十字軍東征,住在鄉(xiāng)間的女人則留在家里,孤獨,隔絕,長年累月住在森林里,在她們的棚屋里,就這樣,因為孤寂,對今天的我們而言無法想象的孤寂,她們開始和樹木、植物、野獸說話,也就是說開始進入,怎么說呢?開始和大自然一起創(chuàng)造一種智慧,重新塑造這種智慧。如果您愿意的話,一種應該上溯到史前的智慧,重新和它建立聯(lián)系。人們把她們叫做女巫,燒死她們。據說有過一百萬名女巫。從中世紀到文藝復興初期。燒死女人的陋習一直延續(xù)到十七世紀。
波爾特:人們在您的電影中,您的書中看到的那些女人,我想到《娜塔麗·格朗熱》中的女人,也就是伊莎貝爾·格朗熱,想到伊麗莎白·阿利奧納,想到《大西洋海灘》里的維拉·巴克斯泰爾……
您認為只有女人才能如此“完全地”居住在一個地方嗎?
杜拉斯:是的。只有女人才會在這里感到自在,完全融入其中,是的,不會在這里感到無聊。我想我穿過這座房子時不可能不去凝視它。我相信這樣的凝視是一種女性凝視。男人晚上回到房子里,在這兒吃飯,在這兒睡覺,在這兒取暖,諸如此類。女人,則是另一回事,有一種狂喜的凝視,那是女人凝視房子,凝視她的居所,凝視屋里的東西,這些東西承載著她的生活,她存在的理由,實際上,對她們中的大多數來說都是這樣,這是男人無法體會的。我曾經說過,當伊莎貝爾·格朗熱穿過花園時,就是這個花園,她穿過花園這件事不會讓您覺得奇怪。伊莎貝爾·格朗熱在花園里,而不是在別的地方,比如一個房間,她不在別的地方,她在這里。她非常緩慢地在花園里行走,這看起來非常自然。如果是一個男人這樣做,如果一個男人以這樣的步伐,如此平靜,如此安詳,人們不會信的。人們會說:他在沉思,因為眼下他遇到了麻煩。人們會說:他在花園里踱步。人們不會說他在花園里散步。人們會說他去那兒想事情。在《娜塔麗·格朗熱》里,這座房子,它是真正的女人住所,它是女人的房子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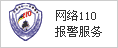


 瑪格麗特·杜拉斯在諾夫勒堡的房子里
瑪格麗特·杜拉斯在諾夫勒堡的房子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