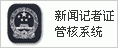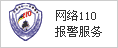在華語電影史上,香港類型電影有著無可取代的重要影響和地位。這些類型電影作品,受益于香港成熟的電影工業(yè)體系和獨(dú)特的“港味”美學(xué),建構(gòu)了龐大的電影帝國,使整個(gè)華語世界都受益匪淺。然而,隨著文化格局和全球結(jié)構(gòu)的變遷,當(dāng)下的香港類型電影已現(xiàn)頹勢(shì)。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,深耕香港市場、扎根香港本土的《正義回廊》接續(xù)著香港類型電影的藝術(shù)傳統(tǒng),隱現(xiàn)著香港類型電影的破局生機(jī)。

《正義回廊》海報(bào)
真相的“回廊”:電影藝術(shù)張力的現(xiàn)代性探索
根據(jù)真實(shí)事件改編,是香港類型電影在票房市場取得成功的關(guān)鍵因素之一。尤其以社會(huì)治安案件為基礎(chǔ)制作的警匪片、恐怖片、法庭片,甚至?xí)a(chǎn)生話題性的影響,如《三五成群》《踏血尋梅》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《神探大戰(zhàn)》等。原型事件為影片提供了足夠的市場噱頭,而如何跳脫現(xiàn)實(shí)事件的桎梏,為已有定論的故事賦予更具張力的“光暈”,則是此類影片藝術(shù)成就高低的鎖鑰。
《正義回廊》取材于2013年轟動(dòng)全港的“逆子弒親案”,話題性自然毋庸置疑。在處理這樣一宗蓋棺論定的案件時(shí),導(dǎo)演團(tuán)隊(duì)采用了現(xiàn)代感十足的不可靠敘事策略,使劇情在真相與掩飾之間不斷橫跳,構(gòu)筑成迷霧一般的回廊,拓展了觀眾的審美空間。
影片一開場就把犯罪者張顯宗弒親的“真相”拋到觀眾面前,頗有希區(qū)柯克懸疑電影讓觀眾“揣著明白裝糊涂”的意味。當(dāng)觀眾將關(guān)注重心放在張顯宗為何弒親的探尋敘事中時(shí),導(dǎo)演又充分借鑒日本電影《羅生門》和美國電影《十二怒漢》的敘事套路,通過第二嫌疑人唐文奇、控辯雙方律師、陪審團(tuán)成員等人的不同講述,把原本清晰可見的案情真相攪成了一潭渾水,敘事的重心從張顯宗弒親轉(zhuǎn)移到了“誰主導(dǎo)了弒親”,解構(gòu)了影片開頭的確定性結(jié)論。
在庭審過程中,涉案人的回憶不斷穿插在敘事進(jìn)程中,又以非線性敘事的破碎性進(jìn)一步混淆著真相。在回憶中,不僅張顯宗和唐文奇各自建構(gòu)著有利于自己的“事實(shí)”,導(dǎo)演也打破了時(shí)空之墻,將控辯雙方律師、陪審團(tuán)成員并置在二人的回憶現(xiàn)場。并通過場面調(diào)度,令二人與銀幕前的觀眾對(duì)視,既在眾目睽睽之下編造“真相”,也將判別真相的壓力給到觀眾,使得影片同時(shí)具備了體驗(yàn)性和間離性,藝術(shù)張力拉到了極致。
故事和敘事確定性的取消,將影片從原型案情中解放出來,進(jìn)入到更大的意義生產(chǎn)空間,一部原本平平無奇的類型電影因而獲得了進(jìn)入精神哲思層面的機(jī)會(huì)。導(dǎo)演對(duì)香港社會(huì)和人情人性的解剖也獲得了漸次登場的機(jī)會(huì),影片的內(nèi)容含量迅速擴(kuò)充,給予觀眾的審美快感和價(jià)值回饋?zhàn)匀灰菜疂q船高,使得影片在票房和口碑兩方面都有了不俗的表現(xiàn)。
當(dāng)然,作為根據(jù)真實(shí)案情改編的電影,真相必然無可更改。導(dǎo)演雖然用現(xiàn)代性的電影語言為觀眾布置了重重迷霧,但也通過具有沖擊力的鏡頭和典型的細(xì)節(jié)捕捉,戳破了唐文奇的故事泡沫,給了觀眾自主破案的成就感。正是在一張一弛、一松一緊的敘事節(jié)奏中,影片的審美質(zhì)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。
“正義”的情懷:現(xiàn)實(shí)主義的批判立場
社會(huì)治安案件所涉及的遠(yuǎn)不止犯案者自身,更有促成犯案行為的系統(tǒng)性社會(huì)問題。因此,以此類案件為基礎(chǔ)改編的影片,多會(huì)以案件為切入口對(duì)社會(huì)生態(tài)進(jìn)行批判性反思,如許鞍華的《天水圍的夜與霧》。《正義回廊》使用不可靠敘事策略剝離附著在故事上的枷鎖,正是為了將故事更好地嵌入香港社會(huì)的縫隙,以“正義的勝利”觀照真相博弈背后的沖突與纏斗。
弒親案牽涉親子雙方,對(duì)于代際沖突問題的反思無疑是影片題中應(yīng)有之義。張顯宗的自我剖白,揭示了暴力行為的發(fā)生邏輯。在一個(gè)充斥暴力的家庭中,張顯宗沒有體會(huì)到父母婚姻關(guān)系的溫暖,也未曾得到公平的親子照料。家庭暴力對(duì)夢(mèng)想的折斷,父母偏愛對(duì)兄弟關(guān)系的扭曲,都撕扯著張顯宗走上最終的犯罪道路。
從某種層面上說,張顯宗是代際沖突的犧牲品。而反諷的是,決定張顯宗生死的卻是一個(gè)充斥著代際沖突的陪審團(tuán)。陪審團(tuán)甫一組建,以白發(fā)蒼蒼的何富為代表的長輩就與以綠發(fā)蔥蔥的鄭家雯為代表的晚輩發(fā)生了激烈的沖突。長輩們震驚于案件的屬性而急于給出判決,并聲稱“天下無不是的父母”,批評(píng)當(dāng)下的年輕人不重倫理、做事輕浮。晚輩們則從自身經(jīng)歷出發(fā),反抗長輩的道德壓力,尋求公平公正的裁決。
代際沖突引發(fā)血腥暴力,而審判這一暴力的仍然是沖突不斷的代際團(tuán)體。影片將這一困局直白呈現(xiàn)在觀眾面前,直指現(xiàn)代性進(jìn)程引發(fā)的倫理危機(jī)及其無解的現(xiàn)實(shí)。在影片結(jié)尾,哥哥張顯祖告知張顯宗,父母在遺囑中給兄弟二人留下了兩套住房,意在淡化張顯宗對(duì)父母的怨恨。導(dǎo)演通過張顯宗激烈的情緒反應(yīng),似乎也想為影片涂抹上一縷亮色。然而,張顯宗長期受到的代際暴力對(duì)待,是否因?yàn)橐惶鬃》烤涂梢钥会寫眩H沖突又是否會(huì)因父輩“我是為你好”“我早就為你安排好了”之類的表達(dá)就消弭于無形,恐怕并不能輕率給出肯定的回答。
在反思代際沖突之余,影片也對(duì)香港陪審團(tuán)制度的運(yùn)作提出了懷疑。陪審團(tuán)成員的選取是隨機(jī)的,但并不是每個(gè)成員都具備基本的法律和邏輯知識(shí),更不是每個(gè)成員都真心自愿花費(fèi)時(shí)間和精力在案情分析上,無法保證裁決的客觀性。而在庭審現(xiàn)場,唐文奇姐姐大打親情牌,一頓嚎啕痛哭惹得陪審團(tuán)成員聞?wù)呗錅I,對(duì)唐文奇的事實(shí)性脫罪起到了至關(guān)重要的影響。這樣的陪審團(tuán)制度,非但未能保證法律精神落到實(shí)處,更為犯案者的脫罪提供了尋租空間。
通過對(duì)現(xiàn)實(shí)問題的批判性觀照,《正義回廊》的價(jià)值與意義就超越了類型電影的獵奇性和商業(yè)性,在情懷共振方面贏得了觀眾的共鳴。
破局指南:回歸“港味”初心
投資1000萬的《正義回廊》一舉斬獲了超過4000萬的香港票房,打破了相關(guān)類型片的票房紀(jì)錄,并獲得第46屆香港國際電影節(jié)最佳男演員獎(jiǎng)和第41屆香港電影金像獎(jiǎng)16項(xiàng)提名,成為香港類型電影的熱議話題。《正義回廊》的成功,無疑為近年來陷入頹勢(shì)的香港類型電影打了一劑強(qiáng)心針。
綜觀《正義回廊》的成功,核心要義在于對(duì)港產(chǎn)電影“港味”的回歸。這種回歸,既有敘事層面的本地化,也有藝術(shù)層面先鋒探索的創(chuàng)造性,更有精神價(jià)值層面對(duì)香港現(xiàn)實(shí)問題的真切關(guān)注。受困于商業(yè)邏輯而不能自拔的香港類型片,只有像《正義回廊》一樣重新接續(xù)港產(chǎn)電影的藝術(shù)精神,才能在日漸內(nèi)卷的華語電影界重振旗鼓。
來源:光明網(wǎng)